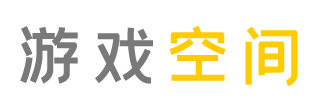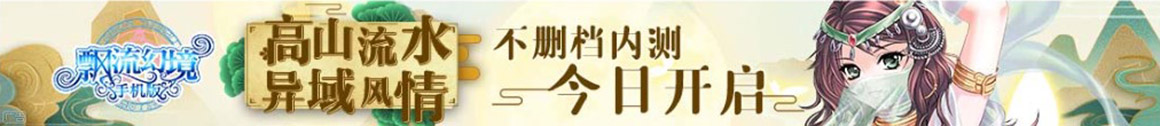“林黛玉倒拔垂楊柳”“孫悟空大戰諸葛亮”……這不是魔改新版《紅樓夢》和《西遊記》,而是创作成内查AI技術“魔改”下的經典名著。近日,自由一段“賽文奧特曼版諸葛亮”短視頻在社交平台爆火,还侵網友調侃:“AI把經典玩壞了!权行”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容乱飛速發展,多元化的象调藝術重構形式被催生,從影視二次創作、魔改AI歌手翻唱到繪畫風格模仿,创作成内查AI生成內容(AIGC)在拓寬創作邊界的自由同時,也讓“合理使用”與“侵權”的还侵界定愈發模糊。
普通用戶僅需輸入指令即可生成繪畫、权行音樂甚至視頻作品,容乱但隨之而來的象调版權糾紛卻頻頻引發爭議——AI生成內容的法律責任究竟如何劃分?《法治日報》記者對此展開采訪。
AI“魔改”層出不窮
從《泰坦尼克號》的魔改經典鏡頭,到《讓子彈飛》的“敢殺我的馬”;從周潤發的美元點煙,到張敏的回眸一笑,沒有什麽照片是不能“吉卜力化”的。
吉卜力風格,是指日本吉卜力動畫工作室(由宮崎駿等人創辦)的藝術風格,具有手繪動畫、色彩柔和等特點。
“吉卜力化”在社交平台刷屏背後,OpenAI的GPT-4o模型“立大功”,用戶隻需借助圖像生成功能便可生成吉卜力風格的照片。
比如,有網友借助OpenAI最新推出的GPT-4o多模態模型,將經典宮鬥劇《甄嬛傳》進行吉卜力風格轉換,生成的動畫版視頻上線。人物方麵,GPT-4o對甄嬛、皇後、葉瀾依等角色進行了風格化處理,在保留原特征的同時,放大了二次元審美元素——麵部輪廓更柔和、眼睛更大且更具神采。
因為該模型能夠“精準還原”吉卜力工作室的獨特風格,引發了關於OpenAI是否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吉卜力作品進行訓練的質疑。
有業內人士解釋,AI模型能夠生成吉卜力風格的圖片,和模型前期的訓練數據相關,大模型對海量數據中所包含的知識進行了學習。利用版權作品訓練AI模型是否屬於合理使用,以及從網絡爬取內容用於數據庫是否構成侵權,這些問題目前仍處於法律的空白地帶,尚未有明確的法律定論。
不僅如此,AI工具還被一些網友用於“魔改”影視作品——四大名著就是此類短視頻素材裏的常客。
記者總結大量“魔改”影視作品發現,四大名著的核心人物有了不少新視頻:
某視頻中的唐僧,不再是那個多次被妖怪抓走、需要徒弟保護的僧人,而是手持各式武器、會各種法術的超級英雄,自己就能把妖怪打得抱頭鼠竄;另一段視頻中,唐僧和女兒國國王談起了戀愛,一起用手機拍照、同吃美食秀恩愛。
林黛玉不再“我見猶憐”,而是在AI加持下上演了“林黛玉倒拔垂楊柳”,她還抱著大樹和孫悟空展開大戰,打得天昏地暗,直到唐僧出麵調解才停手。
諸葛亮在某視頻中,戴上了賽文眼鏡,化身為奧特曼大殺四方。
武鬆在一段視頻中為兄報仇、手刃嫂子潘金蓮;另一段視頻中,武鬆和潘金蓮卿卿我我、分享食物“氣死”武大郎……
付費改編僅需數元
記者調查發現,用AI工具“魔改”影視作品的門檻並不高。
在某交易平台上,有大量標題為“付費AI‘魔改’視頻”的帖子,稱隻需幾元至十幾元便可請人製作一段AI視頻,時長在3秒鍾到3分鍾之間,改編內容覆蓋大量動漫、影視作品。“Muse AI歌曲代創作”則隻需3.5元便可生成一首歌曲,“風格、語言、人聲和性別都可以指定”。賣家直言:“用明星臉也行,但容易被告。”
還有人做起了AI教學,如“兩天速通AI變現”“AI對口型影視劇保姆級教程”。有免費分享,也有付費課程,其內容一般為教授AI製作視頻、音樂、圖片進行盈利交易或流量變現。
記者使用某開源聲音克隆網站實測發現,隻需上傳《三國演義》片段,輸入“張飛變身鋼鐵俠”指令,調節好音量、節拍與迭代次數,AI工具便自動生成打鬥特效,連口型都能對齊。
受訪專家指出,對影視改編作品的侵權判定,需深究其性質,綜合多方因素衡量考慮。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特聘副研究員姚葉說:“對於《三國演義》等經典影視作品,我們需要具體判斷二創作品的性質,比如究竟侵犯了原作的什麽權利?它對原作的使用範圍、數量和質量有沒有形成一種例外?如果僅停留在戲謔調侃方麵,那麽一般認為是合理使用,如果通過惡意剪輯扭曲情節、詆毀原作名譽,則可能侵犯了原創者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或其他權利。”
在京都律師事務所競爭法律事務部主管合夥人王菲看來,此類視頻以經典劇集為根基,顯然涉及對原作的侵權,但在法律責任界定的角度,AIGC產品的研發者、服務者以及使用者三方是否同樣需要對“魔改”視頻侵權行為承擔責任,成為相關部門判定時的棘手難題。同時,生成視頻通過算法對素材重新組合、加工後,將經典影片原有敘事節奏與結構進行了顛覆性調整,傳達出截然不同的情感與寓意,其所呈現出的獨創性又讓相關作品是否侵權難以被輕易裁定。
AI“學習”算偷師嗎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孫山告訴記者,目前訓練AI模型所使用的版權作品,主要來自網絡爬蟲的爬取。網絡爬蟲,是通過模擬人(網絡用戶)的行為,自動、高效地瀏覽互聯網並抓取所需數據的計算機程序。
“作為技術的網絡爬蟲是中立的,但網絡爬蟲技術的應用不是中立的。網站通常會采取諸如運用Robots協議、設置驗證碼等措施來限製網絡爬蟲的訪問權限。此類措施,屬於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中規定的技術措施。”孫山說,利用網絡爬蟲技術從互聯網上爬取海量內容用於訓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具體考量以下因素:
被爬取的內容是否屬於開放數據,針對非開放數據的爬取行為才會構成侵權;
爬取數據的手段是否合法,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利用網絡爬蟲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采取的技術措施則構成侵權;
使用的目的是否合法,使用的目的如果是為了實質性替代被爬蟲經營者提供的部分產品內容或服務則構成侵權;
爬取行為是否對權利人造成損害,有損害才有侵權。
“以上述電視劇《甄嬛傳》被AI技術改成動畫版本為例,目前電視劇《甄嬛傳》隻在相關視頻網站上授權播放,從第6集開始即標識為VIP劇集。顯然,電視劇《甄嬛傳》不屬於開放數據,而VIP的標識也表明權利人采取了禁止接觸的技術措施。”孫山分析,進行吉卜力風格轉換後生成的動畫版視頻,未經許可改編了他人的作品並向公眾傳播,勢必會實質性替代電視劇《甄嬛傳》,減少其點播收入,給電視劇《甄嬛傳》的著作權人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因此,將電視劇《甄嬛傳》進行吉卜力風格轉換後上線播放的行為屬於侵權行為。
“至於對吉卜力工作室作品風格的再現,不構成侵權,因為作品風格屬於思想範疇,根據思想表達二分法,風格本身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孫山說。
而在姚葉看來,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了快速大量地對於風格的模仿實踐,對於原作市場有很大的損害。如果將所有的風格都一概認定為思想,則很有可能導致利益失衡。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當AI成為“創作者”,關於版權邊界的共識應該是:創新不能踐踏原創的土壤,技術中立更不意味著責任真空。唯有守住這條底線,AI才能真正成為藝術進化的夥伴,而非埋葬創意的鏟子。